他的成就绝对不亚于人类防疫历史上包括爱德华·琴纳、路易斯·巴斯德、汤飞凡在内的很多伟人。
上世纪初,沃尔德玛·莫迪凯·哈夫金在法国巴黎和印度地区工作,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支霍乱和鼠疫疫苗。后来,一场大规模的意外中毒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1894年春天,沃尔德玛·哈夫金前往印度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注:Kolkata/旧名:Calcutta,是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地区调查霍乱情况。由于春天是这座城市的霍乱高发季节,因此哈夫金对此事满怀希望。
在去年三月,他带着他认为是针对这种疾病的疫苗抵达印度,但一整年他都在试图努力验证他的发明。在他抵达印度的那一刻起,哈夫金就遭到了一些英国医疗机构和印度公众的怀疑和。他不是医生而是动物学家,并且他是一名在敖德萨(注:Odessa,乌克兰南部城市)接受过培训,在巴黎学习过技能的俄罗斯犹太人,因此很容易受到当时国际上林立的细菌学派别质疑。
哈夫金抵达印度时年仅33岁,却已经在为测试疫苗实用性方面的工作苦苦挣扎。他的第一轮研究需要两次注射2剂疫苗,间隔1周,但他的团队有时特别难找到需接种第2剂的受试者。尽管霍乱在印度传播范围很广,但要受到足够的关注并非易事。根据哈夫金自己的记录,他那年在印度北部为大约23,000人接种了疫苗,“但他们中间没再次出现霍乱,因此无法表明疫苗是不是具有效果。”
直到1894年3月,哈夫金的好运降临。他被加尔各答的医务人员邀请到那里,以帮助在该市郊区一个贫民窟的水箱中鉴定霍乱杆菌。这些村庄由聚集在池塘或水箱周围的泥屋组成,是该市穷人居住的地方。住在这些贫民窟里的家庭集体饮用公共水源,导致他们容易遭受霍乱周期性暴发的影响。
对哈夫金来说,这贫民窟是他新疫苗的理想试验场。每个家庭的人都生活在同样暴露于霍乱风险的条件下。如果他能给一部分家庭中的人接种疫苗,而对另一部分不进行免疫接种,基于足够多的参与者,他最终可能会取得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就在3月底,Kathal Bagan*的贫民窟有两人死于霍乱,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新一轮霍乱的暴发。哈夫金前往该贫民窟,给大约200名居民中的116人注射了疫苗。随后,他的小组观察到了10例病例,其中7人死亡——都是在没有接种疫苗的人中出现。
*孟加拉国达卡的市区,原文为Kattal Bagan,应为作者笔误——译者注
这些结果令人鼓舞,足以使加尔各答卫生官员决定资助更广泛的试验,但说服人们接种疫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英国政府多年来实施的自上而下的医疗计划在民众中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对许多人来说,疫苗的概念仍然是陌生的。
哈夫金的解决方案是与一个由印度医生和助手组成的团队合作,而不是与英国的Chowdry博士、Ghose博士、Chatterjee博士和Dutt博士等人合作。在疫苗领域,他有了一个新的锦囊妙计:公开给自己注射,以证明他觉得自身的准备工作是安全的。
“他(哈夫金)会花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的时间在贫民窟里和印度医生一起工作。他会在人们早上上班前开始接种疫苗,并在人们晚上回到贫民窟后坐在一盏油灯旁继续接种。”
哈夫金在加尔各答贫民窟的工作使他跻身于杰出的科学家之列,他们率先让人们在理解和治疗疾病的方式上进行了深刻和全球性的转变。但与之前的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1749年5月17日—1823年1月26日,英国医生、医学家、科学家,被誉为免疫学之父)和之后的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1914-1995,美国实验医学家、病毒学家。主要以发现和制造出首例安全有效的“脊髓灰质炎疫苗”而闻名)不同,哈夫金的名字从未真正进入公众的脑海,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欧洲。
查克拉巴蒂教授说:“哈夫金是第一个把这种实验医学带到印度这样热带国家的人。他是巴黎的一位科学家,后来来到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他的故事线年,当哈夫金从敖德萨大学
的动物学专业毕业时,他的“回报”是被禁止在那里担任教授,因为他是犹太人。早在五年前,他就在大屠杀中陷入了政治困境。当时,作为一个地方防卫联盟的成员,他曾努力阻止俄罗斯军校学员摧毁一个犹太人的住所。哈夫金被殴打和逮捕,但最终被释放。1888年,哈夫金离开祖国,在日内瓦找到了一份短暂的教学工作,然后去了巴黎,在当时世界领先的细菌学研究中心路易斯·巴斯德研究所
担任助理图书管理员一职。在从图书馆出来的空闲时间里,哈夫金要么演奏小提琴,要么在细菌学实验室做实验。在巴斯德和詹纳工作的基础上,哈夫金发现,将霍乱杆菌通过豚鼠的腹膜腔传代39次,可以产生出一种加强的,或是“高级”的霍乱培养物,然后能够最终靠加热使其减弱。先注射减毒菌株,然后再注射高级菌株,似乎可以使豚鼠对致命的疾病产生免疫力。
在那之前,像霍乱这样的疾病一直被认为是瘴气的代名词——它们在恶劣的空气中传播——并且用Chakrabarti教授所说的“广谱疗法”来对付它们。(“你把一个人放在浴缸里蒸到半死,或者到处喷洒石炭酸。”)但是哈夫金和其他人的工作给疾病管理提供了一个焦点——一种可以培养和减毒的病毒或细菌,可以在人体内被精确地作为靶标。
1892年7月18日,哈夫金冒着生命危险给自己注射了减毒霍乱疫苗。随后是几日的发烧,但他完全恢复了,然后继续给三个俄罗斯朋友和其他几个志愿者接种了该疫苗。当每个人的反应都没有恶化时,哈夫金确信他已经有了一种可实行的疫苗,并能够直接进行更广泛的测试。
但他需要一个霍乱肆虐的地方来进行大规模的人体试验。1893年,时任英国驻巴黎大使、前印度总督弗雷德里克·达夫林勋爵
听说了哈夫金的情况,建议他去孟加拉进行研究。第二年,哈夫金在加尔各答贫民窟的实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他应阿萨姆邦
茶园主人的邀请,为他们的工人接种疫苗。哈夫金在那里对成千上万的种植园苦力进行了大规模的试验,但在1895年秋天,他感染了疟疾,被迫返回英国休养。根据他的记录,当时他已经为近42000人接种了霍乱疫苗。哈夫金后来指出,尽管他的疫苗似乎使病例减少,但并未降低感染者的死亡率。当他于1896年回到印度时,他计划通过测试他发明的新双管齐下的配方来解决这一个缺陷。但是孟买还有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那将使哈夫金永远远离霍乱的研究。
世界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于1894年的中国云南。疫情蔓延到时为英属的香港地区,并从那里通过商船传到了当时的英属印度繁华的沿海城市孟买。1896年9月,在孟买港口的一个谷物商人的住处发现了第一个病例。
起初,英国政府淡化了疫情的严重性,热衷于让一个重要港口城市保持经营。但这种疾病在孟买拥挤不堪的贫民窟肆虐,死亡率几乎是霍乱的两倍,死亡人数飙升。市长向哈夫金求助。哈夫金去了孟买,在那里他被安置在一个小房间和一个走廊里,有一个职员和三个未经训练的助手,他的任务是从零开始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支鼠疫疫苗。
的流行病学家钱德拉坎特·拉哈里亚(Chandrakant Lahariya,流行病学家)说:“他没有过多的空间,人力或设备,但这是他第一次独立工作并有自己的实验室。”“他知道以创纪录的速度开发鼠疫疫苗将使他成为当时科学家中的领军人物。”
12月,哈夫金成功地为兔子接种了预防鼠疫的疫苗。到了1897年1月,他又准备在人身上试验一种针对这种致命疾病的新疫苗。
1897年1月10日,哈夫金给自己注射了10cc的剂量——比他计划在更广泛试验中使用的3cc的剂量要高得多。他经历了严重的高烧,但几天后就康复了。
当月月底,孟买的比库拉教养院(一所关押数百名囚犯的监狱)暴发了鼠疫,哈夫金去那里进行了对照试验。他给147名囚犯接种了疫苗,172名囚犯没有正真获得接种。未接种组有12例病例,其中6例死亡,治疗组只有2例,无死亡病例。
所拥有的一间大的乡间别墅,阿加汗也自愿与自己的Khoja Mussulman社区数千名成员进行接种。在一年内,成千上万的人接种了哈夫金疫苗,从而拯救了无数的生命。他被维多利亚女王封为爵士,然后在1901年12月,他被任命为孟买政府大楼鼠疫研究实验室的主任,该实验室拥有新设备和53名工作人员。
的马尔科瓦尔村(Mulkowel),19人在接种哈夫金疫苗后死于破伤风。当天接种的其他88人都没问题。所有证据似乎都表明53N瓶受到致命污染——这正是41天前在帕雷尔实验室准备的。一个印度政府委员会奉命做出详细的调查,发现哈夫金改变了鼠疫疫苗的灭菌程序,使用加热而非石炭酸,因为这样做会加快生产速度。加热方法已经在世界领先的巴斯德研究所安全使用了两年,但英国人对此并不熟悉,1903年,委员会得出结论,53N瓶一定是在帕瑞尔的哈夫金实验室被污染了。哈夫金作为鼠疫实验室主任被解雇,并被停止了印度公务员的职务。
对判决感到耻辱的哈夫金离开印度,前往伦敦。他以英雄般的速度研制出了一种鼠疫疫苗,并被女王封为爵士,但突然间他发现了自己遭到了同行排挤。要知道这并不是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岗位。
博士说:“那些日子充满偏见,充满了大量的偏见。”他发表了一篇有关哈夫金职业生涯的学术论文。“他不是医疗人员,所以他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因此有很多人在他面前的态度傲慢且自大。”哈佛大学公共卫生教授伊莱·切宁
研究了哈夫金的信件,他写道,“从档案中看不出哈夫金是反犹太主义的公开受害者”,但“若认为爱德华时代的官僚机构完全不受哈夫金是犹太人的影响那简直太天真了”。据切宁说,哈夫金面临着更小的、更私人的斗争——挣扎用英语表达自己确信的态度。在这段时间里,他写的那些信,甚至是写给朋友们的信的背面,都是些“几乎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横线和划叉的内容,而信中的内容都是后来重新仔细誊写出来的”草稿。
马尔科瓦尔事件四年后的1906年,印度政府终于公布了其全部调查的最终结果,认定哈夫金有罪。在阅读了大量文件后,伦敦国王学院的WJ·辛普森教授给《英格兰医学杂志》写了一封信,激动地争辩说,证据指向旁遮普省接种点的53N瓶意外污染。
他写道,首先,瓶子打开时没有一点气味记录,而一个成熟的破伤风培养液会产生一种恶臭和独特的气味。
第二,当15天后对瓶子进行全方位检查时,发现只有少量的破伤风菌。辛普森写道:如果瓶子是在孟买被污染的,委员会“就会在瓶子的残渣中发现丰富的培养物,而不是少量的培养物。”
第三,破伤风在19名死亡患者中病情进展缓慢,历时7至10天,这表明从接种那天开始就已出现轻微感染。由于瓶中已经生成了良好的培养物,它们“可能会受到一种暴发性破伤风的侵袭”。
辛普森总结说,哈夫金受到了“严重的不公待遇”。在他的信发表后,其他人也加入了他的行列。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罗斯
在给《》的四封严厉信件中称英国人“无视科学”,并警告说,除非推翻对哈夫金的指控,否则印度政府将犯有“对最大恩人严重的忘恩负义之罪”。罗斯还发出了另一个今天仍能引起共鸣的警告——如果这个指控被允许成立,即53N瓶在实验室中受到了污染,这将威胁到公众对疫苗的信任,那么这时每周至少有5万人死于鼠疫。
接下来的7年可谓是哈夫金的休假期。在他一生中发表的30篇论文中,只有1篇发表于1907年至1914年之间。他短暂地回到了对霍乱的研究之中,并对开发一种新的“灭活”疫苗产生了兴趣——这种方法后来被普遍的使用——他多次向印度政府申请做试验但被拒绝。1914年,55岁的哈夫金从印度文职部门退休,离开了印度。马尔科瓦尔事件的灾难已经在他身上打上了不可磨灭地烙印,这给他造成的伤害是永久性的。
巴巴拉·霍古德说,“哈夫金应该更广为人知”。“他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细菌学家。”
在1897年至1925年之间,从孟买寄出了2600万剂哈夫金的抗鼠疫疫苗。对疫苗有效性的测试显示,死亡率降低了50%至85%。但霍古德说,他挽救的生命“无法用数字衡量”。“这一个数字太大了。”
哈夫金回到法国,把他的晚年奉献给他的信仰,慢慢的变传统,并建立了一个基金会,为促进东欧的犹太人教育奠定了基础。他从未结过婚,在瑞士洛桑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印度细菌学家HI Jhala写道,他是一个“博学、孤独、英俊、沉默寡言的男人,仍然是个单身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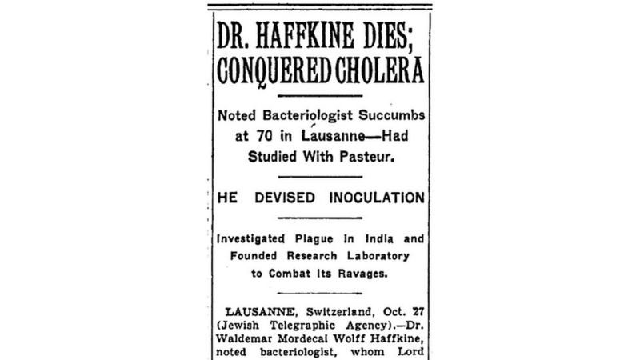
哈夫金于1930年在洛桑去世,享年70岁。犹太电报局发布的一份简短讣告指出,他的鼠疫疫苗已“在印度各地被采用”,他的实验室“向多个热带国家分发了数千剂疫苗”。通告还引用了英国伟大的细菌学家、消毒外科的先驱李斯特勋爵
的话,他简单地称哈夫金为“人类的救星”。哈夫金最初研发鼠疫疫苗的两间实验室现在是孟买KEM医院的一部分。在哈夫金取得突破100的多年后,这家医院正在领导印度抗击另一种流行病——新型冠状病毒。
说:“KEM一直站在抗击Covid-19的最前线,这是对他的一种敬意。”20世纪初,他激励了许多科学家从事疫苗研究,但不知何故,他的贡献被遗忘了。我们不该忘记,哈夫金在一个只有两个房间的实验室和一个非常小的团队中研制出了一种可行的疫苗。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哈夫金的名字确实很突出。1925年,也就是他去世前5年,他的一些支持者游说印度政府将帕雷尔实验室更名为“哈夫金研究所”。政府同意了,这一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当哈夫金收到通知他研究所更名的信件后,他给当时的实验室主任Mackie中校和他的团队写了回信,信中并没有表现出多年在马尔科瓦尔事件阴影下的痛苦。
“在孟买的工作占据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与之相关的一切都不言而喻。我祝愿研究所作代表国家卫生组织一个活跃的工作中心繁荣昌盛,并向全体员工送上祝福。”
后续:本文来源于 BBC News(),为本人闲暇之余翻译所为。有人说,翻译就像戴着镣铐舞蹈,加上鄙人能力有限,若有翻译不当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