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人类消灭了与之鏖战千年之久的传染病天花,这使得人类对彻底消灭各类传染病的信心达到了顶峰。然而,科学家们发现,微生物本身的适应机制使其生命力极度顽强,基因突变和快速的人口流动性都为传染病的蔓延提供了温床,
在近期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推出的《下一次大流行病》专题中,美国《新闻日报》记者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的《传染病卷土重来》 (The Return of Infectious Disease)一文对此进行了梳理。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公共卫生战略的重点一直是消灭微生物。利用战后发展起来的强大医疗武器——抗生素、抗疟药和疫苗——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科学领袖进行了一场军事化的运动,以消灭病毒、细菌和寄生虫等敌人。其目的无非是推动人类完成所谓的“健康转型”,将传染病时代永远甩在身后。在世纪之交,人们认为,世界上大部分人口的长寿期将只结束于慢性疾病——癌症、心脏病和阿尔茨海默症。
这种乐观情绪在1978年达到顶点,当时联合国会员国签署了《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协定。该协定为根除疾病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并预测即使是最贫穷的国家也将在千禧年前经历卫生转型,预期寿命将明显提高。在1978年,对智人与微生物的古老斗争持乐观态度当然是合理的。抗生素、杀虫剂、氯喹和其他强大的抗菌剂、疫苗,以及水处理和食品制备技术的显著改进,提供了一种似乎无所不能的医疗能力。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已知的最后一例天花病例已在埃塞俄比亚找到并治愈。

这种宏大的乐观主义建立在两个错误的假设之上:微生物是生物学上固定不变的目标,以及疾病可以在地理上被隔离。这两种假设都助长了北美和欧洲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一种自鸣得意的感觉:认定人类已对传染病具有免疫力。
实际上,微生物、昆虫、啮齿动物和其他传播疾病的动物都处于一个一直在变化和进化的状态。达尔文指出,某些基因突变可以使植物和动物更好地适应环境条件,由此产生更多后代。他认为,这种自然选择的过程就是进化的机制。
最近,科学家们目睹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微生物适应机制。一些微生物的基因蓝图包含DNA和RNA代码,它们在压力下突变,提供逃避抗生素和其他药物的机会,组织有利于群体生存的集体行为,并允许微生物及其后代在环境中搜寻潜在有用的遗传物质。这种物质存在于稳定的DNA和RNA环或片段中,称为质粒和转座子,它们在微生物之间自由移动,甚至在细菌、真菌和寄生虫之间跳跃。一些质粒携带对五个或更多不同抗生素家族或几十种单独药物耐药的基因。另一些则被赋予了更大的感染力、毒力、对消毒剂或氯的抵抗力,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微妙的重要特性,如耐高温或适应更酸性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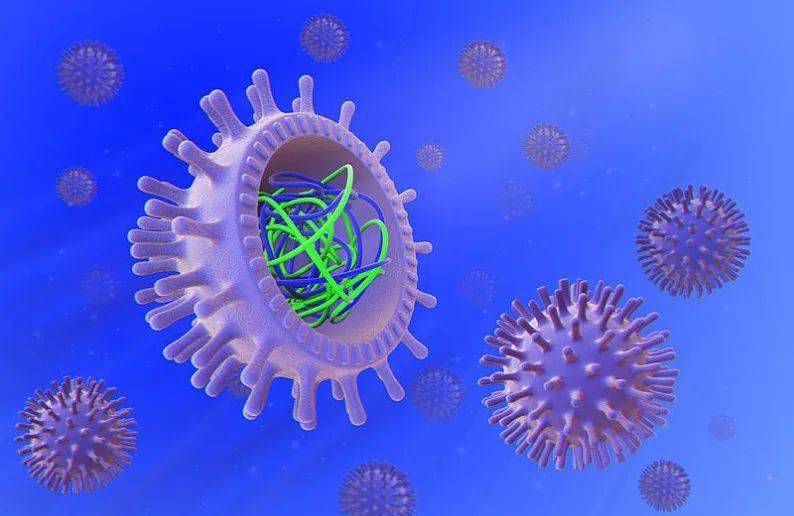
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计的投资政策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经济现代化应该放在首位,健康情况的改善自然会随之而来。今天,世界银行认识到,如果没有对卫生基础设施的投资,一个工作年龄人口中有10%以上患有慢性疾病的国家不可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此外,世界银行承认,很少有社会将医疗保健资金有效地用于穷人,而这些人最大有可能感染传染病。传染病控制方面的大部分成就都来自于国际上的巨大努力,例如联合国儿童紧急基金实施的扩大儿童免疫计划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根除天花运动。
在战后的所有卫生规划中,地理隔离至关重要,但不能再指望疾病继续留在原籍国或原籍地区。早在商业航空旅行出现之前,1918-1919年的流感就在18个月内造成全球2200万人死亡,其中美国有5万人死亡。在1996年,当大约5亿乘客登上飞机的时候,同样致命的流感病毒会有多少受害者呢?

每天有100万人穿越国际边界。每周往返于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旅客达100万人次。当人们旅行的时候,那些不想要的微生物会尾随而来。在19世纪,旅行者携带的大多数疾病和传染病会在长途航海中反映出来,这是他们长途旅行的主要手段。在确认了这些症状后,入境口岸的有关部门可以对感染者进行隔离或采取其他行动。然而,在喷气式飞机旅行的时代,一个携带着埃博拉等病毒的乘客可以登上飞机,旅行1.2万英里,在不被海关和移民局注意的情况下通过检查,又乘坐国内班机前往一个遥远的目的地。但几天后此人仍不可能会出现症状,在病情明显显现前就感染了其他许多人。

1976年,英国和美国政府都花费了数百万美元,试图追踪522名在从塞拉利昂飞往华盛顿的航班上接触到拉沙病毒的美国和平队志愿者。拉沙病毒是一种能导致可怕的出血性疾病的生物。美国政府最终找到了散落在21个州的505名乘客;英国航空公司和英国政府找到了95人,其中一些人也在美国的名单上。没有人被检测出病毒呈阳性。
人类正在全球范围内移动,逃离贫困、宗教和种族不宽容以及以平民为目标的高度紧张的局部战争。从绝对数量和人口比例来看,人们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放弃家园,前往新的目的地。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数据,1994年至少有1.1亿人移民,另外3000万人从农村迁移到自己国家的城市地区,还有2300万人因战争或社会动荡而流离失所。人类的这种快速流动性为微生物提供了极大的活动机会。

加强研究能力、增强疾病监测能力、重振萎靡不振的基本公共卫生系统、定量供应强效药物以避免耐药微生物的出现,以及改进医院的感染控制做法,这些都只是权宜之计。为了国家安全,人们需要采取更大胆的措施。
一个优先事项是寻找科学有效的方法,利用聚合酶链反应(通常被称为DNA指纹)、实地调查、化学和生物出口记录,以及当地法律文书来追踪新的或再生的致命生物的发展,无论是天然的还是生物武器。努力的重点不仅应该是对人类有直接危险的微生物,还应该包括那些可能对农作物或牲畜构成重大威胁的微生物。
大多数新出现的疾病首先是由初级保健一线工作者发现的。目前,美国没有一个系统能让一线工作者通知相关当局,并确保他们的警报被迅速调查。目前,世界各地的互联网接入都在改善,一笔小小的投资将为医生提供一条通往国际卫生当局的电子高速公路。

只有三种疾病——霍乱、鼠疫和黄热病——受到国际监管,这使联合国和各国当局可以在必要时干预全球货物和人员的流动,以避免跨境流行病出现。世界卫生大会是世卫组织的立法机构,它在1995年日内瓦年会上建议联合国考虑扩大受管制疾病的清单,并寻找新方法来监测疾病的广泛传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基奎特爆发的埃博拉疫情表明,一支国际科学家团队可以动员起来,迅速控制一场在偏远地区由非空气传播媒介造成的局部疫情。
洛克菲勒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约书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认为,应对疾病威胁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大体上是直截了当和合乎常理的,而且具有普遍的国际意义。“坏消息是”,他说,“这些解决办法都要消耗大量金钱。”而各级政府都在削减预算,特别是保健预算。达斯汀·霍夫曼曾在电影《极度恐慌》(Outbreak)中扮演一名疾病控制科学家,他赚的钱比美国国家传染病中心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年度预算加起来还要多。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15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